
崔元植 (韓)
CHOI Won-shik
东亚文学共同的家
崔元植 (CHOI Won-shik)
1.盖房子
这次做的主题演讲是我的告别演讲。从10年前举行的第一次论坛开始,到第二轮重新开始的今天,回顾东亚文学论坛的历程,连曲折坎坷都在烁烁发光。不仅如此,把所有的迂回曲折称为论坛的肉体和灵魂也不为过。我们一起建设的东亚文学论坛这个家,可不是有什么著名建筑师趴在桌子上一个人做出来的海市蜃楼,是将要入住这房子的三个国家的作家们集思广益后盖起来,住着住着又不断修建,而且每当有新人作家入住时就会修改,不停地推迟完工之日,即完成立即变成未完成的“共同之家(the common house)”。梭罗说的“生活的无意识之美(a like unconscious beauty of life)。”恰似对我们东亚文学论坛的评价。
这是能让我们切身体验到超越国家、国民、语言之界线的十年。仔细想想,“超越”一词不是没有语病。如果在两者关系中,超越一词似乎可以成立,但在三者关系中却无法超越。因为三者已经构成了世界。具有“横跨”之意的中国语“跨”,可以很好地说明我们这个论坛。进入论坛的瞬间,我们就跨坐在中国语、日本语、韩国语之间了,更何况这三个语言在中国的《诗经》、日本的《万叶集》、韩国的《三代目》之后,历经一千多年的切磋琢磨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文学语言。进入这个论坛生活的作家们,在陌生的时间和陌生的空间里,虽然猝然间背负了在漫无边际的语言之间的联络员责任,同时因为陌生读者的支持,把这份责任转化为隐隐的喜悦。在此我要骄傲地说,围在这“共同之家”周围的韩中日三国读书共同体,他们发出的虽然低沉却十分坚决的喝彩声,才是推动论坛发展至今的关键后盾。(后略)

铁凝 (中)
TIE NING
时间和我们
铁凝 (TIE NING)
各位来宾,朋友们:
大家好!
十年前的这个丰硕的季节,首届东亚三国文学论坛在首尔举行。十年后的今天,第四届韩中日东亚文学论坛再次来到首尔。十年前,参加论坛的三国作家们彼此尚属陌生;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逢时, 我们熟稔的目光和神情都在告诉对方:感谢时间,让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么久。
我在这时想起了中国一句老话:“十年树木”。这句话出自中国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意思是一株树苗长成大树需十年时间,更指树木成林的不容易。“树”在这里作动词用,说的是养育和培植。东亚文学论坛走过了十年的时光,在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这棵关于文学的论坛小树已成长为健康的大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如果可以把论坛的每一位作家比作一棵独立的文学之树,正是你们的集结,才使这论坛成为文学之林。而每一次论坛不断有新的作家加入,一株株挺拔、峻朗的新生之树和大家比肩而立,更使这文学之林变得格外富有朝气和活力。(后略)

平野啓一郎 (日)
HIRANO Keiichiro (PHOTO©MIKIYA TAKIMOTO)
站在作家和作品、读者和现实的缝隙之间
平野啓一郎 (HIRANO Keiichiro (PHOTO©MIKIYA TAKIMOTO))
作为日本的一个作家,作为日本作家团的团长,能够参加第四届东亚文学论坛,我感到无比荣幸。
再次,谨向为这次大会的举办付出诸多努力的韩国、中国两国的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第一轮的论坛,即2008年第一届首尔大会、2010年第二届北九州大会以及2015年第三届北京大会,举办得十分成功,然而事实上,日本方面难以再参加那以后的论坛。
当然,对于这个论坛的重要性,日本的实行委员会和韩国、中国方面一样,对此坚信不疑,主要问题是来自于财政方面。
然而,在摸索第二轮论坛的举办方式的过程中,韩中两国总是以充满热情的温暖鼓励赋予我们勇气,最终尽管采取的是韩中共同主办的形式,但仍然给日本方面与以往一样的人员配额,邀请10位作家来到了首尔。
两国的组委会诚挚认真地表示,对于这个论坛来说,日本作家的持续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对此,我心中的感动无法言表。第四届论坛的主题是“21世纪的东亚文学—心灵的纽带”。而这个论坛的存在本身就是“心灵的纽带”的体现,对于这一点,我想以深深的谢意加以强调。
这个论坛至今已有十年,而我有幸全程参加,诸多的回忆难以一一言尽,然而在此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印象深刻的一段小插曲。
在举办完第一届首尔大会后,我们前往春川,在那里举办了几项文学活动。其中有一项是纪念与春川颇有渊源的金裕贞作家的野外活动“金裕贞文学之夜”,那天是10月3日。
那一天举办了歌舞表演,还在宽阔的公园里提供有烤肉,十分尽兴。唯有一点,当天非常寒冷,预备上台朗诵作品的我一直瑟瑟发抖,前来聆听的其他作家和当地居民似乎也觉得非常寒冷。
在我旁边坐着的是莫言先生。按照安排,作家们需按照顺序朗读作品,等待期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对话,在结束之后,我不知不觉间用英语说了一句“真冷啊”,他一副十分认同的样子,一边笑着,一边用手轻轻抚摸了几下我的上臂。
早年我曾阅读过莫言先生的《红高粱》和《酒国》。而那段时期,我正在阅读他作品的日文译本《转生梦现》,正好读到转世为牛的主人公见到阎王爷时,向他抱怨转世为驴的部分。
莫言先生在日本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和近乎于走向神坛的地位。能以这般丰富的想象力写作的小说家到底是怎样的人,对于这一点,我一直怀着敬畏的好奇。而这样的人轻轻摸了我的手臂,这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在第二次北九州大会时,莫言先生访问了我的母校东筑高中,和我一起举行了面向在校学生的公开对谈。莫言先生得知这所高中是日本演员高仓健的母校时,十分惊讶。他告诉我,在他青年时期,同龄人都为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追捕》而狂热,而他却为英姿飒爽地骑马搭救主人公的中野良子而着迷。
这些都是跟文学毫无关系的小事,东亚文学论坛已有10年的历史,是各国作家们特别的交流平台,以这样的方式了解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各国作家们的品性,这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以后在阅读他们的小说时,这样的记忆就会不时在脑海里浮现。(后略)

权汝宣 (韓)
KWON Yeo sun
韩国小说家K的简历
权汝宣 (KWON Yeo sun)
1965年,我在韩国南部的安东市出生,至今都不曾离开过韩国这片故土。除了母语韩语之外,对其他语言都不太精通,不曾想过要用其他语言写写文章,在写作中也没有考虑过我的作品该如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一直以来,我都只是在韩语表达的框架下进行了写作,也只是对韩语中的语言意象比较了解。
我虽读过一些翻译过来的中日代表作家的文学作品,比如鲁迅、村上春树,但在中日文学上的造诣谈不上深,想来这样的我却得以在中日韩论坛上发表主旨讲话便觉有一些不堪重望。但换个角度考虑一下,那种认为自己已经无所不知的想法也许比知道自己有所不懂更加危险,于是我决定接受自己的不足,并做好我所能做的。因此在今天,我想要借此机会,向各位简单描绘一下我作为一名韩国小说家所经历过的韩国文学。
我是在1996年进入韩国文坛的,在韩国,首次在报纸或杂志上登载自己的作品被视为作家入坛的必修课。进入文坛之后虽然没有一直都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写文章,但在名义上,我作为小说家也已经入坛22年,在这22年里,我所走过的韩国文学之路,包含着一些无论对韩国文学造诣多深的中日文人也无法理解的、特殊又充满矛盾的东西,虽然我的经历不能说在韩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但所有作家的经历似乎都有一些大同小异,我相信通过我对我个人经历的介绍,能够将韩国文学中隐藏的共性向大家展示出来。
我入韩国文坛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是韩国现代文学充满奇妙的接合与断裂的时期。从世界史上来看,社会主义阵营开始没落,韩国80年代民众文学逐渐消退,其空白的一边是回忆80年代的所谓“后日谈文学”,一边是向内挖掘个人内心世界的新的文学形态。我的第一部小说徘徊于两种文学之间,形式上采用后记文学体,而内容上则注重表现怪异的内心世界。可以说,这部小说包含着我后来在文学路上的奋斗与彷徨,更大胆一点说,便是作为“386一代”的我,苦斗与彷徨已经开始萌芽了。
“386”在韩国是非常有名的数字组合之一。这一表达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出现,原本是计算机系统用语,后来逐渐用作指称韩国现代史中挥之不去的一代人。所谓“386一代”是指90年代进入30岁而立,80年代上大学读书,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发展至今,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有趣的是,“386”以“现在—20岁—出生”这样的倒序时间排列起来,一个偶然的命名,却成为这一代人命运般的标签,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个数字会变成“486”、“586”甚至更多,但后面两个数字永远定在那里,这也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本质与前面的数字无关,而“8”与“6”才是关键,即80年代的时代变革以及60年代韩国战争结束后出现的婴儿潮,这些标志性事件都为这一代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后略)

邱华栋 (中)
QIU HUA DONG
构建东亚文学地理学的新景观
邱华栋 (QIU HUA DONG)
从地理上看,以乌拉尔山脉到大高加索山脉一线为东部边界,西抵罗卡角,再由诺尔辰角南跨至马罗基角,这就是伟大的欧罗巴大陆。最近二、三十年,欧洲致力于为自己构造全方位的一体化机制,以形成更强大的欧盟共同体。虽然有薄薄的一层世界主义思想,但很少人认为他们真的是流动的、没有国家的欧洲人。在地理上,地球是接近正圆形的,以西半球和东半球作为一种简易区分,但现代性的全球形象则几乎是被“the West and the Rest”(斯图亚特·霍尔)所界定的。“欧洲和亚洲”正是这一二元对立结构的具体变形。现在我们相聚在这里,就是为了谈论亚洲以及我们共同的东亚。
亚洲广袤分散,而东亚紧凑,中、日、韩自古以来就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地理意义上的东亚,除了三国,还包含朝鲜与蒙古,也有人认为越南曾内在于儒学文化圈,因此也是广义上的文化东亚。但是中日韩的组合自有其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现代化”。“东盟+3”的框架,正旁证了把中日韩视为一个可整合的现代化区域共同体的逻辑,而东亚文学的地理学,也由此显露出轮廓。(后略)

中岛京子 (日)
NAKAJIMA Kyoko
21世纪的东亚文学/心灵的纽带---风吹过的地方
中岛京子 (NAKAJIMA Kyoko)
这次给我的主题是“21世纪的东亚文学/心灵的纽带”。
我不加思索地答应了演讲,后来才意识到其重大,有些困惑为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对于我这种三分钱作家而言,是个棘手的主题。在韩语或中文里,不知道是否也有“三分钱作家”这样的词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稿酬低,写着没什么价值的小说的作家。以前的三分钱相当于现在的100日元左右。当然我也没想过做100日元的工作。
因为对困难的、太大的东西没有天分,所以我打算从简单容易的小事开始。几年前,我曾在某本杂志上,发表了我自己与邻国韩国如何邂逅的文章。我打算以此为基础,以文学为中心,再加上与中国邂逅的故事,以及在此延伸线上的事情,用这种方式克服难题。因为这次活动的举办国是韩国,所以我就先从韩国篇开始介绍。
与韩国文学的邂逅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韩国文学是《尹福的日记》。大概是70年代初的时候。这是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出版的第一本日译朝鲜文学。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男孩边照顾弟妹边积极向上的故事,这与同一时期读过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贫苦少年的故事和形象类似,完全感觉不到是在看外国小说。当时,觉得韩国离我们很远,不像现在这样。
读《尹福的日记》时,是小学的时候,当时我和父母及姐姐四个人一起住在东京近郊的公寓小区里。我记得当时家里还有金芝河的诗集。父亲是专攻法国文学的学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书房里,但他很喜欢金芝河。父亲除了阅读诗集外,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但当时的学者或媒体人多多少少都会对韩国的情况感兴趣。
80年代是韩国动荡的时期。几天前,我看了一部《出租车司机》的电影。宋康昊在电影中扮演了一位搭载德国记者尤尔根•因兹彼得从首尔前往光州的出租车司机,电影剧情十分感人。说点题外话,大家知道吗?德国记者尤尔根•因兹彼得用相机拍摄取材的同一时期,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也以身犯险前往光州取材。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有1980年5月的报道为证。据说这位记者为拍摄风景或其他目的,碰巧待在首尔,他的上司说,光州出大事了,叫他去调查,于是他坐出租车前往光州拍摄。和彼得一样,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听到“把你看到的情况告诉全世界”的声音,所以他拼命地冲破了警察的警戒线,将事件报道了出去。当我知道,有日本记者报道了邻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如果我能对当时的事情有深刻印象的话就好了,但很惭愧,我的记忆只是一片茫然。当然也不是全然不知,但也是后来阅读了韩江的《少年来了》和赵世熙的《矮子射上去的小球》等作品后,才了解光州民主化运动及之前的韩国氛围。
(后略)

金爱爛 (韓)
KIM Ae-ran
光和债
金爱爛 (KIM Ae-ran)
一听到‘传统’之类的话语,我会想起已去世的人。会想起他们给予我的和没有给予我的,以及无意中给予的东西。同时,还会想起收到的和想拒绝的,以及无意中收到的东西。
尘封许久的东西大多都在一直变小,变小,直到从黑暗中消失。可是当想起以前的故事时,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联想到光。这可能是在古老的故事中,某盏灯光在情节最为紧张的时候,像手电筒突然照在陌生的脸庞上,使心中的紧张像感光胶片一样残留下来;也有可能是故事中总会有光,而且有火堆的地方就会有嘴和耳朵的缘故吧。
我的经验和智慧虽有不足,但是通过书本遇见了许多的光芒。其中有着探索深海的探照灯,也有着信念燃烧的火焰,还有人们做饭时燃起的火苗和枪口里的火星,也有包括所谓受难者留下来的余光或人们往往会称为鬼火、魂火的葱绿色的神秘东西。
其中就有到现在都让我感到一种原始性恐惧的火光,这就是李清俊的中篇小说《传闻之墙》中出现的手电的光芒。此时我脑海中浮现作品中充满恐惧的一家人,半夜里突然走进一群人,问他们:“你站哪边?”需要作出生死抉择的他们无法看到对方的模样。在我看来,那些在耀眼灯光下的追问和暴力是韩国现代史的重要场面,那是因为延续到现在的韩国诸多矛盾背后,一直晃动的正是那盏手电筒所发出的灯光。(后略)

全成太 (韓)
JEON Sung-tae
死語事典
全成太 (JEON Sung-tae)
晚上出门上大号时,蜷缩着身子蹲在地上,看见门前晃动的柿子树枝会感到恐惧,看见自己的影子移动也会害怕。那是颇为寒冷的夜晚。我总是叫着奶奶,要奶奶回答,还会时常担心奶奶是不是在看别的地方。
常言说给鸡拜晚年,孩子们半夜起床出门上大号的病就会好。给鸡跪拜,其实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也不是什么害羞难堪的事。鸡笼里的鸡受了礼,也欣然地咕咕地叫着。
听说吃了流星会长命百岁,而且听说还有人捡到过。那晚,流星也像箭一样滑落,落在了后山的松树林。在那里,叔叔曾徒手抓过鹌鹑。
流星陨落的地方
放在心上
本想隔日去看
想着,想着
就这样长大成人了
(郑芝溶的散文《流星陨落的地方》前言)
这是一篇很好地体现韩国语传统韵味的散文。我认为这篇散文算是韩国散文中的翘楚。“我”、“奶奶”和“自然景物”三个不同的主语互相影响着,构成三四个短句,而且还容易表达感情。然后又将其组合成一个长句,如浑金璞玉般纯粹而通顺。
三段的构成形式像小孩子的口头禅一样琅琅上口。在“给鸡拜年”这种民间风俗的贯穿下,故事情节由晚上上大号突然转向流星。整个故事的展开缥缈又充满画面感。散文中,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体现了既满足又孤寂的感情。这篇散文不仅展现了韩国语口语体的生命力,也很好地体现了语言的传承。
这是一篇罕见的散文,现在近乎绝迹。在近百年社会的快速发展中,韩语的使用者就像新新人类一样,从文字构成乃至于与自然的相处方面都丢失了纯真的好奇心以及亲近自然的属性。(后略)

苏童 (中)
SU TONG
传统:民间想象力的利用
苏童 (SU TONG)
谈论传统这个话题,可能是在谈论古人与前辈,也可能只是在谈论你自己。我想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写作立场,无论你是传统的致敬者还是叛逆者,终其一生,不过是围绕着传统这幢巨大的建筑忙碌,修修补补,敲敲打打,其实都是传统的泥瓦匠。
传统给人滋养,其滋养的方式与途径千变万化。当人们在感恩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的时候,潜台词往往是感恩李白杜甫,感恩苏东坡与李清照,感恩《红楼梦》与《金瓶梅》,这其实都是感恩正典,也就是传统这幢建筑雕龙画凤的华彩部分。我们很少去探寻这幢建筑的地基,地基怎么样了?地基当然是被建筑覆盖了,它一直都在,只是不被注意。地基里有什么材料?当然多得不胜枚举。我想,应该有通常被列为另类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甚至未被文字记录的某些儿歌、山歌、民谣。那里有人类对世界最原始的文学想象力,来自民间,它究竟是如何滋养我们的?我们其实快忘了。换句话说,当一个作者对世界的想象以最杰出的训练有素的文字呈现,并且结出正果的时候,当人们高喊一部杰作诞生了的时候,可能也正是一支山歌失传的时候,在伟大作家越来越多的时代,很多来自民间的想象之花正在山野间默默地枯萎。(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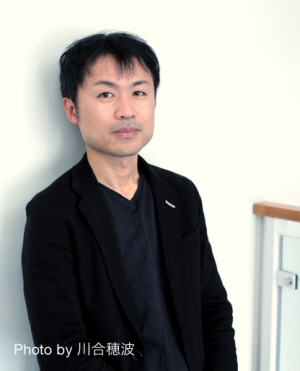
阿部公彦 (日)
ABE Masahiko (PHOTO©KAWAI HONAMI)
日语和声音的文化
阿部公彦 (ABE Masahiko (PHOTO©KAWAI HONAMI) )
大约在一年前,我就表明了对于大学入学考试政策的反对意见。也一直在推特上写评论,并出版了《史上最差的英语政策——一派胡言的的“4种技能幌子”》这本书,同时也有很多机会接受媒体的采访或者投稿。也许正归咎于此,受到了一些甚有交情的友人们的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平时所做之事到底是怎么做的?”
但是我认为关于入学考试这个问题与文学和整个文化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如果简要说明政策基础中的东西,大致想法如下。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在公司里“可以使用”之人。当今日本职员们缺乏的是运用“可使用的英语”的能力。所谓可使用的英语就是“能够说的英语”。想要熟练掌握“能够说的英语”最佳的方法就是引入民间的考试…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最终的关键词是说。用更为熟悉的用语来说就是,“就算无法阅读英语文章,那也进行一些英语对话吧。”
在这样的英语政策下,相当一部分人会点头认同“嗯,也许就是这样。”其背后所隐藏的是会话和文章是不同的这种想法。因此在语言学学习中出现了应该“读解”还是“会话(说话)”这种二分法。虽然这次的“4种技能”这一用语经常被使用,“4种技能”不过是一种掩饰,实际上争论的焦点是应该“读解”还是“会话”,这才是重点。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事实上不久前有机会参加国际研讨会,向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们说明了日本入学考试政策的现状,大家都说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要执着于“文章”(written English)和“会话”(spoken English)这种二分法。甚至还提出或许这就是“理智主义”和 “反智主义”之间的对立这样的意见。
事实上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我所想到的是从明治到大正时期的“言文一致运动”。在日本,由于当时所谓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背离很大,以主张引入西洋小说的文学者为中心,他们为了填补两者间的差异作出了各种尝试。这些领域超越了文学的领域,涉及到了其他的体裁,最终引发了日语书面语的特性,甚至是言论形式的巨大变革。
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已经变得很小,但是两者的间隔并没有完全被填补。

若松英辅 (日)
WAKAMATSU Eisuke
传统在何处
若松英辅 (WAKAMATSU Eisuke)
世界现在频繁出现右翼化倾向,提倡回归”传统“。日本也不例外。空洞的传统主义的弊端已经威胁到了教育和宪法修改等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对于重视传统的人们来说,他们找不到可以思考“传统”是什么的理论依据。在没有思考传统为何物的状态下,主张回归传统的人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如果重视传统只是单纯地指追溯时间上的过去,那么最终我们只能回到文化诞生之前所谓“原始”的状态。即使将这理解为极端的言论,但如果将传统理解为单纯的时间现象的话,那该追溯到何时这个问题将一直存在。
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可以发生在所有存在思想、文化、宗教性活动的地方。传统主义以进步主义的失败为契机得以萌芽。这被简单地通过原理主义(fundamentalism)相连接。同时,我们知道当传统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想融合时,会引发一场无法控制的疯狂的运动。“传统”的复苏,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方法,将会产生不仅是吞噬人类,更会吞噬某种文化时代的威力。
试想一下通过文字的起源去追溯“传统”这个词语所蕴含的意义。
根据汉字学者白川静所言,“传”字除了“传达”的意思外,还有“拓宽”或者“搬运”、“遗传”、“传播”的意思。

张康明 (韓)
CHANG Kang-myoung
我们可以做到“差异”
张康明 (CHANG Kang-myoung)
之前读过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小说家写完小说后马上死去,才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就读者的角度而言,小说家的解释,会扰乱读者的正常阅读。
我认为这句话颇有道理,但我还不想马上就死去。虽然有点尴尬,但是在不妨碍读者正常阅读的前提下,我将围绕我的短篇小说《蚊子》,和大家探讨今日的主题——“差异”。“这只是作家的一家之言,希望不要受到干扰”,这是今天我对大家的嘱咐。
短篇小说《蚊子》刊载于我的系列小说集《罗米埃尔的人们》(2012)。小说集的故事发生在首尔西大门区新村洞,讲述的是住在想象中的公寓楼“罗米埃尔”第八层的人们的故事。该小说集由相互关系比较松散的十篇小说组成,短篇小说《蚊子》是其中的第二篇作品,故事讲述了该公寓楼802号发生的事情。
这本小说集里的作品风格相对灰暗,并带有一定的幻想色彩。小说《蚊子》也不例外,看到最后,读者都搞不懂到底是身体麻痹的中年男性在想象着小女孩的情景,还是被称为小女孩的年轻女性在想象着身体麻痹的中年男子。除此之外,小说又穿插了住在隔壁的听觉障碍人的故事和患抑郁症的孕妇的故事。
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刚满37岁。当时我对韩国社会的牢固的群体关系很感兴趣。1960年开始到2000年左右,韩国以相当快的速度完成了产业化和民主化。这段剧烈的社会变化时期,也给当时的年轻人们带来了很多机会。但是在2000年以后,社会发展动力开始变得不足。
还有,就像在座的各位所经历的那样,自2000年开始,许多国家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并进入世界化的行列中,这个世界化又在不同的层次上实现了一体化。换句话说,政治和经济都朝着民主主义和修正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和消费方式倾向于追求企业的合理性和效率性的“麦当劳”方式,文化领域则朝向重视“年轻、富有、SEX”的美国式大众文化。这样一来,在发达国家里出现了相似的生活模式。慢慢地,人们穿着相似的衣服,吃着相似的食物,听着相似的音乐,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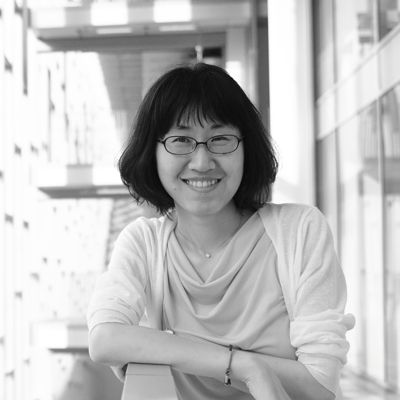
陈恩英 (韓)
JIN Eun-young
东亚,差异与心灵的纽带
陈恩英 (JIN Eun-young)
下面我们来思考一下,韩•中•日三国作家在一起见面时所说的"差异"是什么样的图景。难道这是像马蒂斯作品中经常看到的蓝色、黄色、红色或者浅绿色一样能造成强烈对比的差异吗?还是像春天争奇斗艳的梅花、樱花、杏花这三种花一样的差异呢?这些花在那些不熟悉的人看来,相似得难以区分,而对于熟悉的人来说,它们之间的差异迥然,将这些花混淆不清的事实,反倒让他们觉得奇怪。我们东亚人就像是同时表现出相似与差异的这三种花一样,看似相似,实则不然。
在能够俯瞰到春天白色小花朵的研究室的书架上,我取出了里尔克的诗集,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形象。里尔克从一模一样的房与房之间看到了不同的时间穿越。这就是里尔克所想的差异的形象。
看吧,他们将同样的可能性如何
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并展开,
那就像我们从两个一模一样的房与房之间
看到不同的两个时间在穿越。
- 勒内․马利亚․里尔克, 「姊妹」 部分
长期以来我们居住在一个叫做东亚的一模一样的房间里。但是我们将一模一样的可能性,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接受并展开下来,这一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实地暴露出来。虽然我们在相似的环境中长大,可我们却像气质完全不同的姐妹一样截然不同。那么,我们就像拥有很强的个性并对彼此了如指掌的姐妹那样,能够友好相处吗?我当然希望如此。但是里尔克在《姐妹》的下面接下来的段落中,对她们的命运有着不同的看法。诗人不是在说温暖的愿望,而是告诉你冷冷的现实。(后略)

张炜 (中)
ZHANG WEI
林与海与狗 ——《父亲的海》写作背景
张炜 (ZHANG WEI)
想起过去,心中往往出现并列一起的三部分:林子,大海,狗。它们纠集于我的童年。林子在海滩平原上,狗和各种动物在林子中,我则徘徊在它们之间。
上学后童年就被约束了。但只要走出校门,我们就会撒腿跑向海边。海滩上林密人稀,只有很少几个村庄散在林中。猎人、采药人、渔人,是他们在林中活动。关于林子的传说很多,这些传说的主题从许久以前就形成了,主要是劝人不要伤害动植物。它贯彻了人与物平等的观念。比如说口口相传的故事中,人往往不如一只动物善良和聪明,也不如一棵老树更值得敬重,等等。
国营林场的工人们对我们很重要,反过来也是一样。他们给我们故事和吃的东西,让我们看他们的狗。果园的人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人与我们好的时候特别可亲。好的季节是冬天和春天。那时他们修土埂、浇水和剪枝,在鲜花中劳动,人也和蔼。他们开我们的玩笑,互赠吃物,与各位家长来往时笑脸相迎。但果子成之后就不行了。那时他们声气变粗。因为我们要想法弄一些果子。现在回想,人在小时候对樱桃、李子和苹果的思念真是不可思议。一定要偷,要摘。吃果子的欲望盖过一切。人的生命在那个阶段可以概括为“果子时代”。(后略)
。

曹有云 (中)
CAO YOU YUN
心灵的纽带:父辈们卓越的东亚诗歌书写
曹有云 (CAO YOU YUN)
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谈到三位东亚诗人。因为在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卓越的现代诗歌书写中清晰地昭示了关于东亚诗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给予我们深刻的感发和长久的激励。他们和我父亲一样都出生于二十世纪30年代,我称呼他们为“父辈”。
日本国诗人谷川俊太郎(1931——)、韩国诗人高银(1933——)、
中国诗人昌耀(1936——2000)。
毫无疑问,他们三位前辈都是各自国内卓越的诗人,乃至是伟大的诗人。其中,高银和谷川先生还健在,昌耀先生已于2000年3月——千禧年曙光照临这个孤独星球的春天便匆匆告别了这个世界。
我以一名普通读者的身份,按照中国传统(也是我们东亚传统),从最年长者谷川先生谈起吧。
知道谷川先生是比较早的,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得到了他的诗集,是在格尔木一家文具店图书角购买到的,但由于几次搬家,诗集“潜藏”于“书海”,很难找到,好在后来又购买到了他和他的知音译者田原先生共同遴选,收入他不同时期代表作的新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后略)

岛田雅彦 (日)
SHIMADA Masahiko
人类啊,就要这样灭亡了吗?
岛田雅彦 (SHIMADA Masahiko)
冷战时期世界末日的画面,是由人们对核战争的失败以及失败后的世界的想象而形成的。如何在被核辐射污染的废墟中生存、定居,这类问题的答案可以在电影《疯狂的麦克斯》或与之相似的《北斗神拳(日本制作的漫画和动漫电影——译者注)》里看到,那些画面无一不是没有法制状态下的弱肉强食。
有了核战争以后,化学燃料消耗过度导致的全球变暖、流行性疾病、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和大规模的海啸以及核电站事故等都是加剧“大灭亡”的原因。我们常常在救援生命、防灾生活、城市基础设施重建等方面充满想象力。在战争中或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在地震或大规模停电的情况下,人类的生活水平会倒退到100年甚至是200年前。人类能够适应“小危机”,但是对于“大灭亡”,就如字面意思,关乎着人类和文明的灭亡,甚至能令人对之后的生活产生绝望。
即便如此,肯定会有人劫后余生。这些人并不想活在罪恶感或义务里,也不想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所以他们会试图保护丢失的文明或者重建文明。对于对高度分工已经习以为常的现代人来说,那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接近于踏踏实实摸索产业革命的过程。刚开始的狩猎采集生活,是去搜寻城市便利店或超市剩下的食品、生活必需品,之后便会为收集水源、食品、燃料、信息等而焦头烂额。于是,这些劫后余生的人开始过滤江水,寻找柴火。不久后,他们必须要开始农耕,接着制作各种各样的道具、配件、机械,渐渐提高劳动效率。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会想着拥有燃料或电力;为了与其他生存者接触,会创造移动、运输或通信条件;生病时,也变得需要用药。如果要修复电力,就利用流动的江水进行小规模的水力发电或太阳能发电。最近狩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有复兴的趋势,但人们并不只是单纯地追求兴趣,而是在为消费文明衰退后的危机做准备。当然,文明的重建不可能从零开始,积累了过去的智慧或睿智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会得到重建。
无法使用网络或电脑,图书馆便成为了文明重建方法汇集的信息中心。公园或空地被用于生产食物,茅坑再现,任何人为了生存都不得不劳动。因为待在城市不利于生存,所以人们分散各地,组建成小团体或共同体,构建成一个分工体系,最终形成一种最适合生存的生活方式。(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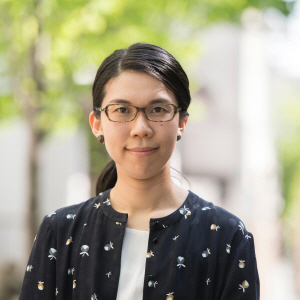
小山田浩子 (日)
OYAMADA Hiroko (PHOTO©SHINCHOSHA)
差异的交错
小山田浩子 (OYAMADA Hiroko (PHOTO©SHINCHOSHA))
我的小说经常被别人用“奇思”“异想”等词语来评价。比如作品中出现图谱中所没有的动植物时,或者非常熟悉的生物做出奇怪的行为时,又或者对于这些人们表现出的反应不一致时更是如此。完稿的小说不管被如何解读都是让作者庆幸的事情。但从作者的立场来看,所有的一切,即使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现实和幻想之间是没有差异的。这不是指作为现实寓言的幻想性要素,不管哪一个都是实际上存在过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写进小说里的所有事物就是现实本身,但是大部分读者会认为这些都是想象的,是幻想的,其实,这些都根植于我的改变了形式的、或者直接的经验和体验。
这次出版的《寻找叔母》这部作品是以梦中看到的情景为基础来写的。虽然梦只出现在我的大脑中,但却是很明显的现实。我确切地看着它,闻着它并感受着它,并感到惊慌。从梦中醒来想它们写下来,所以就马上写了。以这种以梦为基础的方式写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此外,小说中出现的动植物也是根据各种梦境中看到的来写的。梦中的生物会与各种事物交错在一起,或者缺少某部位,如果注视它就会改变形态或者消失。但是其质感和湿度我是确切感受到了。而且在这种梦境中发生的事情或者生物的奇妙感,比如在附近田野转悠的虾或者蚂蟥,又或者是TV和图片中出现过的远在外国的色彩斑斓的蝴蝶或者长着像葫芦瓢一般的鼻子的猴子,奇妙之中又没有任何的差异。不同的是,实际当中是否看到过,感受过,体验过它们。写我与在TV中看到的奇妙的猴子一起生活的故事,也许这是不可能的(尽管看到了TV中奇妙的猴子这个事实可以写)(后略)

邦玄石 (韓)
BANG Hyeon-seok
平壤航班上的母语考试和韩国文学的未来
邦玄石 (BANG Hyeon-seok)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36年。
1945年, 独立和分裂,战争,停战65年。
2018年,( )
在( )内,应该用韩语填入什么内容?
4月27日,在板门店会面中,韩语被转播到整个世界。朝韩领导人见到了无需翻译就能自如对话的唯一对象。我虽然不知道韩国的其他作家们如何看待这一瞬间,但我内心是非常激动和复杂的。尽管我是使用母语创作的作家,但是在我的文学世界中,使用着同一语言的另一半人的生活却从未出现。不仅如此,我对描述这另一半人生活的朝鲜文学作品也不太了解。在我们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我们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涵盖母语的一半的“不健全的作家”。
通过直播观看文在寅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的对话,我想起了2005年的平壤。
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开的朝韩作家大会上,我作为实务代表,从驻北京朝鲜大使馆取得访问证,乘坐高丽航空Js152次航班飞往平壤顺安机场。当时与我同去的还有一名担任民族文学作家会事务次长的后辈。在飞机上拿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入境许可证”时,我感到十分为难。飞机广播提示正在飞越鸭绿江的时候,许可证上的“国籍”一栏还一直困扰着我。大韩民国、韩国、南韩、南朝鲜......最终我还是写了“南”。
直到“您将马上到达顺安机场”的广播响起为止,我还有一个选项没有填写,就是“民族”。韩国民族、朝鲜民族、韩民族、檀国民族(檀国为古朝鲜——译者注)......这是一个难题。我问了坐在隔壁的一位女性,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打开了她的许可证,上面写着一个我没有想到的词——朝鲜人。我看到了她的答案,虽然和她是一样的民族,但我却没办法和她作出同样的回答。最后我在飞机到达顺安机场前写下了“我们民族”。(后略)

崔恩荣 (韓)
CHOI Eun-young
没有战争的未来
崔恩荣 (CHOI Eun-young)
上高中的时候,我在《韩民族21》中读了有关越南战争的特别报道,之前我学到的都是韩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因此这篇文章使我大为震惊而悲伤。那时我才知道,战争包含着对老百姓的大肆屠杀、强奸和严刑拷打。自从了解越南战争之后,那些之前只是无心浏览的战争新闻越来越让我在意。
22岁那年,我去越南旅行的时候曾见到一位越南修女,我对她说“我对韩国军人在越南所犯下罪行深表歉意!”她却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别放在心上。”那一刻,我们两人共同感受的那种心情让人难以忘怀。那一刻,我们两人都释怀了,那种从内心深处产生的共鸣,使我至今都难以忘怀。我24岁的时候曾因工作原因在越南待过两周时间,那期间越南朋友邀请我去他们家里,他的爸爸非常热情地欢迎我,还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现在想来都是无比珍贵而美好的回忆。
短篇小说《xinchao,xinchao》的人物原型就是当时我所见到的热情的越南人民,小说发生在1995年德国一个叫普劳恩的小城镇。在那里韩国人“我”们一家和越南人翠儿一家相遇,并且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次两家一起吃饭时“我”很自豪地说:“韩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学校就是这么教育的。但是韩国小女孩的一句话,在这次稀松平常的聚会上引发了胡叔叔一家和“我爸爸”之间的矛盾,胡叔叔一家曾经受过的伤害并没有得到爸爸的认同。
“我”的朋友翠儿那天曾这样说:“听说是被韩国军人杀死的。听说他们杀了妈妈的全家人,就连奶奶,还有当时还是孩子的姨母都被杀死了。在妈妈的家乡还有记录韩国士兵罪行的‘韩国军憎恨碑’”。“我”的妈妈一直低着头说对不起,而爸爸则开口说道:
“我说什么呀?一定得说,是我们做错了?为什么要你站出来说道歉的话?你算什么呢?”然后他对被韩国军队杀掉全家的阮阿姨说道:“难道不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吗?我一直向你恳求谅解,您才甘心吗?”爸爸的哥哥是在越南战争中战死的,他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他不愿意去理解胡叔叔一家的遭遇,也没有真诚地去道歉,最终两家人因为此事渐行渐远。(后略)

雷平阳 (中)
LEI PING YANG
关于未来的写作
雷平阳 (LEI PING YANG)
在我的写作经验中,“未来”一词具有审美性质,可它又是可疑的。于审美性质的范畴,它意味着尚未呈现的一切,想象中的一切和虚空的一切,这几乎就是诗歌写作过程中全部的精神家当和永远也了却不掉的天国梦。而它的可疑之处又在于,我们处于现在,处于虚弱的写作与思想贫血相互矛盾的旋涡中,处于对现实失控和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崩溃与惶惑中,却又总是号称我们的写作只针对未来,是为未来的人们而写作,仿佛未来真的就是所有因为写作而悲伤地死去的写作者的天堂。
1946年,俄裔天体物理学家伽莫夫乘坐美国空军的飞机,辗转各地进行演讲。有一天,当他在纽约的一家咖啡馆静坐时,于一个真实的瞬间,亲眼看见了大脑之中原子和亚原子在旋转,看见分子,行星、银河系和超星系团在旋转,于是便在咖啡馆账单的背后,用数学公式将自己看见的一切迅速的记录了下来。可事后,他却无法辨认他当时一蹴而就的潦草的字迹,更是无法获取那一瞬间神赐般的秘密信息。德国艺术家克鲁格和里希特在复述这一事实时,说伽莫夫因为无法辨认自己过去的手迹,“他再也不曾如此精确地看见这个世界”。(后略)

甫跃辉 (中)
FU YUE HUI
大 风 歌
甫跃辉 (FU YUE HUI)
我家后院边,有好多片竹林,其中一片竹林边上,有一棵高大的苦楝树。苦楝树粗壮的主干直直地朝上生长,直到高过竹林了,快两层楼那么高了,才伸展开枝桠。那枝桠,几乎要探到小路对面的王家的屋顶。每到春天,苦楝树开花,五瓣的紫色花朵缀满枝头,细细密密的,蓬蓬勃勃的,轻微地晃动着,几乎遮没了叶子。
春天里大风吹,吹得竹林呜呜呜响,竹林俯仰,枯叶满天飞。这不像是春天来了,倒像是冬天回来了。但细细一看,纷飞的干枯竹叶里,夹杂着一些小小的紫色花朵,旋转着,降落伞似的,悠悠忽忽落下,细碎的星子般,铺满整个后院。
后院起初是泥地,后来变成水泥地,几年以后,水泥地开裂,裂口处长出牛筋草和葎草。杂草疯长,我们到后院少了。又过些时候,水泥地荡然无存,又回复了泥地……不知道如此反复了多少次。院墙也如此,起初是土坯墙,墙上有瓦。土墙倾圮后,修了空心砖矮墙,不知多久,砖墙开裂,裂缝处长出绿绿的臭灵丹(翼齿六棱菊),眼看就要倒伏。不记得多久以后,家里又修了新的院墙……院子变化着,正如大风吹动季节的变动。
变动得厉害的,又何止我家这小小的后院?(后略)

中村文则 (日)
NAKAMURA Fuminori (PHOTO©KENTA YOSHIZAWA)
未来
中村文则 (NAKAMURA Fuminori (PHOTO©KENTA YOSHIZAWA))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小时候,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人,但我仍觉得人很可怕,而且每天都过得很痛苦。人类究竟是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因为活得很痛苦,所以常常产生这样的想法。高中时,这样的痛苦达到了极限,导致我再也无法去学校。
日本的学校都要求穿统一的制服。打扮相同的人,在同一时间,走进同一个房间听课,这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却感到很可怕,觉得无法承受。
如果无法适应集体生活,那么未来的人生就会令人担忧。我今后要怎样活下去?十几岁时,我曾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当时,是文学拯救了我,是太宰治和芥川龙之介等作家拯救了我。
当然,并非只有我有这样的苦恼,但当我明白这件事情后,还是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这也是我沉迷于文学的契机。后来,我阅读的倾向也扩展到陀斯妥也夫斯基、加缪等世界各国的作家。
虽然我不喜欢人类,但是却从人类写的小说中获得救赎。这种想法渐渐消除了我对人类的不信任。许多文学家一直思考探求的“人类是什么”、“世界是什么”等问题,一直留在我心中。每当我写小说时,我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后略)

上田岳弘 (日)
UEDA Takahiro (PHOTO©SHINCHOSHA)
被“未来”所吸引
上田岳弘 (UEDA Takahiro (PHOTO©SHINCHOSHA))
不知不觉,这件事已经过了16年。当时,我还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和大部分文科生一样,想付出最少的努力,高效率地取得学分。当时甚至还有一些有志的学生发行并销售杂志,告知哪些科目容易取得学分。不知道这种文化,现在是否还存在,但我想应该还是存在的。不管怎样,这些东西都是轻易不会改变的。
也是在大学时期,我第一次感觉到了邻国的存在是如此亲近。我所在的国际法研究小组,计划让全体组员去韩国访问。以东京为基准来看,韩国是地理位置比冲绳更近的又近又远的国家。这是由指导教授主导策划的活动,甚至还给从韩国来的留学生安排了《韩国语特别讲座》。虽然是自由参加,但大学生们本来就时间富裕,所以很多组员都参加了。这可能是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那一年发生的事情。两国的距离突然变得越来越近,但与物理距离相比,当时的日本对韩国的感觉,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亲密。
据说,为了学会不熟悉的语言,学习的人必须回到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跟着邻国的留学生读例文。我并没有参加那次韩国旅行,因此也没有听过特别讲座。
从参加的组员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议论。
“韩语的发音很吸引人。”
“女讲师朗读韩语的声音也很动听。”
“卫生间在哪里?这句话一定要背下来。”
听到组员们热闹讨论,我当时都有点后悔没有报名参加韩国之行。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偷偷去听一听《韩国语特别讲座》。(后略)

金錦姬 (韓)
KIM Keum hee
所以,依然无法得知
金錦姬 (KIM Keum hee)
作为一名编辑,我度过了自己20多岁的时光。那时,如何制作一本好书、作为出版界从业人员应积累怎样职场经验,以及如何亲手制作出畅销书等疑问一直困扰着我。为此,我听取了某个团体举办的出版讲座。讲座由政府提供资助,每周有一天要提前下班一小时,所以,这个自我开发的时间是公司给予了照顾才得以实现。讲师大部分是出版社的社长,而听讲座的人,则像我一样都是出版社的职员。那时笼罩着我们的午后昏昏沉沉的氛围,至今记忆犹新。如果已经制作出了畅销书,肯定不会再到那里接受教育。所以说,如果大家都热情饱满、态度积极的话,也许会更为奇怪。与最初的决心不同,我也慢慢地沉浸在那个空间中异常的无力中。就在那时,担任讲师的某出版社社长说了一句稀奇的话,一句我平生都无法忘记的话:这世界上存在着三千名奇怪的读者,所以无论制作出什么样书,都会销售一空。对于做了一系列连初版册数都消化不了的策划的我来说,虽对那句话半信半疑,但耳朵却不自觉地竖了起来。(后略)

沈甫宣 (韓)
SHIM Bo-Seon
天下有诸多新鲜事物
沈甫宣 (SHIM Bo-Seon)
读者们总是让我感到很惊讶。他们总是用惊人的方式来解读我出于某种意图写下的诗句,甚至是连我自己都忘掉意图的诗句。他们经常用宏观的角度对我狭义的作品赋予历史性和社会性,同时用微观的视角对我宽广的作品赋予活生生的生命。
有时读者们很较真,执着于个别句子和单词。甚至还会盯着数字:为什么不是14或者16,而是15?对这些批评家们小心谨慎的评论,读者的解释有时具有果断的跳跃性。对于读者而言,和家族史有关的隐喻会成为早年朝鲜战争时期南下的“游击队”的故事。为什么读者有时会很执着,有时又会果断地进行解读呢?
因为读者们不愿意被束缚,他们不需要文学史和批评理论这类学术交流的参考框架。有些时候即使他们使用了这种参考框架,也不是将其作为解读诗句的主要方针,而只是作为可供选择的手段和资源。在运用这些概念时,读者们不会考虑学术共同体,他们会想象着把自己发现的秘密告诉别人并为之兴奋。
因此对于读者而言,解读和经历不是分离的。我在我的作品中曾写过没有任何意义的“预想的彩票中奖号码”,但是一个读者却“实际”买了那个号码的彩票并且“实际”中了5000韩币。读者可能将彩票号码赋予了某种神力,或者有可能单纯因为有趣买了那个号码。在一个书店举办的“读者见面会”上,那个读者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我认为我的诗并不深奥,但是在非常独特的解读下有了这种独一无二的“现金化”经历。我对那个读者开玩笑说道:“那5000元您是不是要分我一点啊?那里面有我的股份吗?有的话是多少呀?”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后略)

徐坤 (中)
XU KUN
寻 找 读 者
徐坤 (XU KUN)
三十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还不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谁,也根本无从考虑自己的文章是写给谁看。那时只凭着一股子蛮力气,认真写作,一味向前,尚无虚张声势的顾盼,只如春水初生,春潮初长,借一股强劲的东风,那就是一种叫做“青春”的东西,任内心的汪洋,恣肆摇曳于笔尖之上,一泻千里在北京干旱的沙滩上流淌。
然后,我看到读者蜂拥而至。各种各样的读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种看客,许多姿态,有在沙滩上纳凉看热闹的,也有恪守传统的严正批评家。有的仰望,有的俯视,赞美鼓励,评头论足。无论忠言逆耳,还是赞誉过度,我都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照单全收。
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用文字挖掘出的一条心灵通道,豁然间畅通、抵达了。它抵达了这个世界,抵达了他者的心灵。因为有了“读者”,我跟这个广大的世界有了精神上的牵联。因为有了读者,我在北京这座两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才不显得孤单。有读者在,就有作家在;有作家在,便有读者在。二者构成牢不可破的对象化关系。作家使读者满足了某种对现实和历史的“共诉”需求;读者使作家们普遍有了现世存在感。(后略)

王威廉 (中)
WANG WEI LIAN
写作在召唤和创造着阅读
王威廉 (WANG WEI LIAN)
仔细反省自己的写作,我惊奇地发现,我自一开始写作,脑海中几乎没有读者的位置。我对谁会读我的作品完全没有考虑。我并非自负之人,恰恰相反,这应该缘于我的谦卑而漫长的阅读史。我很可能当不了作家,但我无法想象自己不再阅读,完全沉溺在现实当中。阅读是区别于现实的另一个空间,在我看来,写作和阅读所进入的是同一个空间。我愿意借用诗人米沃什对文学的一种定义:“第二空间。”这个空间不是机械地凌驾于我们的现实空间之外,而是与我们的现实空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
作为读者,我读了各个国家大量的文学作品。每当读到韩国、日本的文学作品时,那种感觉与读其他国家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我心里会涌起神秘的亲切感。韩国、日本作品中那种对于家庭成员的格外关切,以及含蓄的情感表达,都能激起中国人心底的微澜。我们自然可以说那是儒家文化的一种特征,但我们可以往深层思考,为什么会有儒家文化、又为什么可以接纳儒家文化,一定是基于那种生命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深层相似。我更愿意从这种深层的相似性上去理解韩国、日本的作品带给我的那种亲切感。(后略)

岛本理生 (日)
SHIMAMOTO Rio (PHOTO©HAYATA DAISUKE)
读者
岛本理生 (SHIMAMOTO Rio (PHOTO©HAYATA DAISUKE))
投稿参加新人文学奖活动,作为作家正式进入文坛,已是2001年17岁春天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年龄不大的原因,所以到现在我的小说题材主要还是以恋爱为主。
我的其中一部代表作《爱,不由自主》在去年被行定勋导演拍成了电影,那是一个关于高中教师与自己教过的学生之间的爱情故事,所以在介绍作为作家的我时,常常被称为恋爱小说家。
不过,比起恋爱,我更关注“看似是恋爱的其他东西”。
我的读者主要是和我年龄相仿的80后以及大学生、高中生等比较年轻的女性,面向这些读者,我的小说以非表面的性暴力或疼痛为背景来写。
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少女们来说,成人的巧妙的控制欲和性欲,看起来与恋爱极其相似。
我的青春期在90年代后半期到零几年的东京度过,当时日本处于泡沫经济末期,正是余波逐渐消散的那几年。
虽然泡沫经济在90年代后半期已经结束,但是东京仍然陷在余波的旋涡里。
在那个时代,千方百计赚钱的冷漠与对时代末尾的不安同时存在。“世纪末”这样的话语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的气氛。
女高中生为了钱和成年人发生肉体关系,衍生出来“援助交际”一词还流行一时,这些都是在我高中时代发生的事。
我记得我当时在涩谷的街道上散步,一个成年男子突然向我搭话:“多少钱可以做那个?”像这样若无其事地询问的情况并不止一次。我还听说,有的女孩子已经表示拒绝了,却还差点被强制拉走。
虽然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在那个危险的时代下,扭曲的价值观如此横行肆虐,给当时的女性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后略)

柴崎友香 (日)
SHIBASAKI Tomoka (PHOTO©KAWAI HONAMI)
距离与读者
柴崎友香 (SHIBASAKI Tomoka (PHOTO©KAWAI HONAMI))
仍记得,我第一次如今天这般和外国作家们坐在一起交流是在2010年12月,当时也是在首尔举办类似的论坛。当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文艺杂志企划刊登各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那也是我第一次访问首尔。三个国家的作家在讲台的座位上,我用日语做简短的演说,然后翻译成韩语。由于当时没有会日译中的人士,所以要先翻译成韩语,再翻译成中文。到第一个阶段为止,还能通过听众们的反应知道正在谈论哪一部分,到了第二阶段,完全无法把握。
在那之前,我还认为翻译、读外国文学,这些离我遥远的事情正在慢慢向我靠近。但是在当时,我知道了翻译其实是把我的意思带离我而传播出去。而且现在我还认为,不只是翻译,创作小说时,从下笔的那一刻起,也许我表达的意思就离我而去。在那远去的支点处正是读者所在之处。(后略)